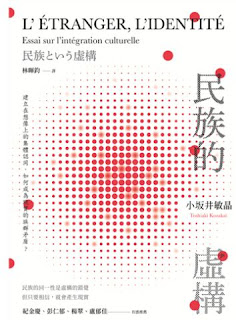民族的虛構:建立在想像上的集體認同,如何成為現實的族群矛盾?( L’ ÉTRANGER, L’IDENTITÉ. Essai sur l’intégration culturelle ,小坂井敏晶 )
如書名,這本書談的就是"民族"定義的虛構性.未翻開書之前,可能會預設這書該談的多少會涉及批判性,讀完後卻發現不是這麼一回事.
討論民族議題的書籍往往很虛偽,若不是政治意義上的鼓吹,便是認同意義上的假面和諧,而且些喜歡以一種光明和平的口吻與描述出現.但兩者內涵往往一致,隱藏其中論述不是排除"障礙",要對統一認知進行鬥爭,便是直接殺戮.究其原因倒單純,因為實際上無法用一種絕對無例外的方式定義出''民族"的範疇,篩出一個純種的民族出來,其間往往涉及定義任意性,或是概括的暴力性,不在定義範圍內的少數個體,若不是笨被強迫硬逼塞入範疇,便是將其割除,只有這兩種方式能創造出表面名義上看似純粹的單一民族.但這樣似乎讓談民族議題最終都是為了區分彼此,方便後續的辨別,且不管論者是基於多元民族主義,還是單一民族定義,不願接受或是同意這種定義的,下場都很慘.
所謂的''民族同一性"似乎是個虛幻?作者小坂井敏晶是個日裔法國人.正是這樣的身份讓作者有機會從自我凝視,到觀察他者,興起的對民族這個議題的興趣.從文本中我們發現作者的幾個觀察,一個是對日籍朝鮮人的狀態觀察起了疑問,這些人之所以會遷徙到日本居住生活繁衍是源於殖民時期,現在在日本的朝鮮人基本上都已經不會說韓語,與原先的母國也沒有任何聯繫.他們一方面還是會面對若有似無的被歧視,卻也無力或無法連結原母國,以至於只能留在日本,但是許多留日朝鮮人並沒有改變國籍,認同上依舊當自己是朝鮮人,作者以為從某些觀點上來看,他們明明已經是日本人,但實際上,不管是他們的自我認同,還是部分的日本人眼中,他們依舊不被認為或不自認是日本人,還有他自己早長居法國,卻經常被人視為是一個日本人.單一民族的論點如此,那麼從美國英國那種多元民族,擬制想像民族的觀點來看呢?顯然從愛爾蘭人,蘇格蘭人的例子,及,美洲原住民,都與被認定的美國人或英國人區別居住,分別明顯,看不出具有同一性,因此顯然找不到一個絕對無瑕不能排除其他少數的民族定義方式.面對同樣移民法國,但來自中南半島移民在法國的受認同度,與自我認同度,都遠高於來自阿爾及利亞等北非移民,即使向法國這種普遍主義定義民族的方式,依舊不能讓民族同一性成為一種絕對無誤的可能,於是作者自然思考起''民族同一性"的虛無性,虛構性,的荒謬性.
當作者講出民族同一性虛構的荒謬時,讀者可能以為他要開始批判人類這種虛構的虛偽與惡劣時,作者反而回來要確認虛構是必要的,必然的,且虛構才是符合於人類世界觀點的,作者於此提出了三種觀察,這三種觀察都涉及關於民族的定義.首先是認為民族中必有某種超越各個個人的本質的存在,所謂的"民族精神",它是超越歷史的實體,假設這樣的提起確實存在.第二種方式是將民族視為保有血緣的大家族,就是血緣論.第三種則是主張只要能維繫某種這要的文化元素,就可以做為民族連續性的依據.這是因為隨著時間的流逝,人類群體的成員必然會發生變化,成員的集合本身是不可能存在同一性的,想要讓這種同一性合理的延伸產生連續性,就必須要找到某種個人與個人之間共同的臍帶,這三種方式便是過去人們定義民族所找尋的共同臍帶方式,從作者的觀點不論是血緣神話,還是文化連續他們其實都是在歷史長河中逐漸不斷地融入其他,透過核心不變,邊緣改變等讓人無法在短期內發現改變的型態在演進,實際上,並不存在不變的同一性,實際上其中真正不變的就是一直在變,只是那種變化極小,用數學的眼光來看,就是微分,所以有一種同一性的假像,實際上血緣或文化歷史長河的演進像是積分,它是一塊面積,即使某些東西的名稱不變,它的內在可能與早先定義時大不相同,也就是說用實體不變的同一性定義民族,本身就是一種虛構,虛妄,人類就是不斷的在無意識中製造虛構,將斷續的現象同一化.若不是這樣的運動,連續性不會出現在我們眼前,所以人類認為的民族記憶或者文化的表象沒有一刻具備同一性,人類本質沒有同一性這種東西.這些東西都是動態的,所謂的民族文化或者血緣其實是一直不停的被解構加入新的元素再建構而生的.
即使我們明白了民族定義的構建充滿了虛構性,那麼人們為什麼會相信它呢?作者提出了一種說法稱之為''預言的自我實現",這是由社會學家Robert King Merton經由實證發現的,這種觀點大意上是說人總是會抱著某種先入為主的觀點,與外界接觸,對象的意義並非獨立存在於觀察者,行為者,而是每次在不同情境下,由對象與其觀察者,行為者的關係所決定,而觀察者,行為者只能夠過他們習慣的表象,他們所構成的表象,來認識,理解現實.於是,即使一開始表象與現實不符,因為表象而產生的行動最終將扭曲現實,而為偽們所認定的表象正當化,不論在正面,或負面的的意義下,這樣的事態都會發生,這便是預言的自我實現,這種自我實現的預言被作者認為在韋伯的資本主義與新教倫理中有類似的觀點.因此雖然民族是沒有虛構就無法建立同一性的現象被勘破,但最終還是成了人類從根本處規範生存的現實.不過,作者雖解構了民族的虛構性,卻認為與其解開這種虛構的誤解下可能的錯誤,還不如相信與更近一步利用這樣的虛構性,只要能找到一個有利於民族和諧組成共處的方式與說法即可,這是作者破解民族的虛構,卻沒有呼籲要消滅虛構說法的原因.
要利用民族虛構性,作者接著揭露了對共同體責任的構成看法,及共同體與個體的關係,主要是之前提出的對在日朝鮮人,在以色列國境中的巴勒斯坦人,或者法國的北非或阿拉伯裔少數民族融合問題,他最終提出開放式共同體的建議試圖藉此來解決當前民族國家內,民族國家不此之間所遭遇的衝突與民族困境問題.作者對於民族的實體責任的看法首先摒除了整體論,既然本質上民族不具備實體的同一性,要硬套某種特定的責任於共同體中的每一個人其實是虛妄的,他以為過去對於社會對民族集體責任看法的失敗是源於盧梭的契約論,這種契約觀點強調國家或共同體的連續性,但是如果共同體中的人們否定了這樣的契約責任,問題便會發生,這種契約論的本質是將社會視為是由各原子個體所組成,將人類視為個體自主且合乎理性的存在,他以為這種個人主義透過了契約解構了個人與社會關係原先的直接聯繫關係的定義,及社會關係影響駕馭著個體的思考行為,改主張人是因為最大利益,而與他者進行各式各樣交換,於是透過契約聯繫著個體間的關係,最終形成社會關係,這是一種源於新古典經濟思想而來的見解,作者則排拒這種看法,主張以涂爾幹的主張社會決定論為基礎,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重視歷史上形成的社會規範對人類思考的束縛,認為人是受到了社會與歷史條件制約而存在的,但是社會決定論與社會契約論都將社會與個人視為對立的兩項,差別只是一個以個人為起點,一個以社會為起點,在作者看來都無法補抓到社會與個人之間的動態關係.作者提出的方法是不將集體視為實體,而是努力地從個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角度來理解集體,將集體現象視為各個個人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一方面承認社會只不過是個人的集合,同時觀察社會成員相互關係的產物,脫離個人主觀意願與控制的過程.,個人現象與及體現想以循環的方式相互影響,宛如螺旋一般,並在這個基礎上嘗試構建開放的共同體的概念.
在作者動態論觀點之下,不把集體的同一性當成是一個看做固定不變的具體事物,而是視為社會成員之間相互作用的運動.因此要理解同一性的變遷時,必須將同一性分為核心價值與周邊價值來思考,同一性隨時間的變化,就是人們在短期內認為屬於核心部分事項較不願改變,但是周邊的部分,則容易接受異文化的要素,因此亦文化的衝擊首先由周收因為如此,接受了異文化衝擊的自己實際上已經產生了客觀的變化,但主觀上人們仍認為自己維持著民族與文化同一性.因此為了維持著民族同一性的假象,多元文化主義的主張容易因此產生公民依照其民族或文化出身而彼此分離的現象,而普遍主義之下,少數族群經常會受到壓迫,所以作者以動態觀點的演變觀念提出開放的共同體,一方面強調不壓抑移民社會中少述派的文化,這樣的影響是雙向的,少數派也能侵蝕多數派的周邊,一起構築一個新的世界觀,不論什麼出身,所有公民都自發地接受異文化及其同化所帶來的改變,只是一昧的保護特定少數而不改變各自的價值觀,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多數與少數間的關係是流動與充滿活力的,少數派理論的影響有斬斷主流主體多數支配,壓迫,歧視的惡性循環的可惜性.
雖然說作者的用心可觀,但現實政治的權力來源本質靠的便是多勝少,所以民族切割作為一個議題,是有利於想要藉此強調差異而贏得多數選票的政治組織的,而且以今日世界分裂的狀態,這個多數勝甚至只需要相對多數即可,如此更增添了許多政治人物或黨派主張民族區別或定義民族絕對同一性的動力,明知它幼稚可笑又落伍,但它就是現世,是我們每天都能在媒體上看到聽到的真實,所以利用虛構真的會如作者所期那樣光明,個人是有些懷疑且相當的不看好的.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