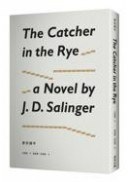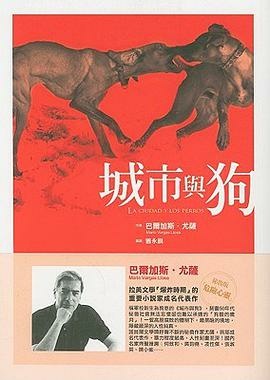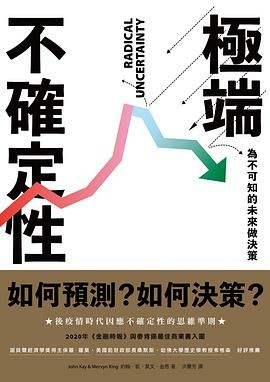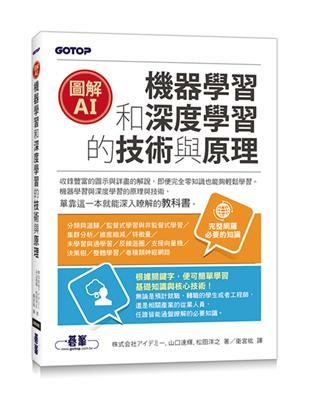斯德哥爾摩情人(LOS AMANTES DE ESTOCOLMO,Roberto Ampuero)
為這次美洲小說的主題準備的書不少,但不確定能否在這次都看將它全部讀過,從福克納的"聖殿","押沙龍押沙龍","去吧,摩西"."我彌留之際",馬奎斯"愛在瘟疫蔓延時",魯爾福"佩德羅.巴拉莫",阿圖里亞斯"玉米人',"總統先生',波拉尼奧"2666",富恩特斯"阿爾特米奧.克羅斯之死",科塔薩爾"萬火歸一",阿特伍德"盲眼刺客',翁達傑"英國病人",數目太多,每本的份量又不少,除了部分實體書外其他多是早年別人給的pdf檔,所以不確定能否全部看完,畢竟看pdf傷眼,只好看到哪本就算到哪了,就不列閱讀順序了,照例,不會一直看小說,還是會插入其他類書籍.
接在"城市與狗"與"麥田捕手"後的是一本智利作家的作品.書名叫做"斯德哥爾摩情人",也確實是個發生在瑞典的故事.但作者Ampuero是智利人,他曾經因為政治原因流亡到歐洲20年,也曾移居瑞典4年,回國後曾擔任智利的駐外大使,後又出任外交部長,這篇小說得主角背景與他的政治背景與起伏是相關的,所以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本反映他自身經歷的作品.儘管拉美曾經政治動盪,不知為何竟有好幾位知名作家都能當上自己所在國家的部長,總理,甚至總統,雖然他們的政績普遍不佳,又貪污頻傳,但文學作品的卻四未曾受影響."斯德哥爾摩情人"是本帶著懸疑的偵探小說.
就通俗的意義上,這疑似一本偵探小說,一對在斯德哥爾摩生活的夫妻,先生偶然間發現妻子私藏一些情趣衣物,又經常與一些他不熟識的異性偷偷聯繫與見面,先生克里斯托瓦懷疑妻子馬賽拉有外遇,於是他開始跟蹤馬賽拉,果然發現她與一些男人見面.就在此時他的鄰居馬爾庫斯的老婆瑪莉亞病逝,但是他波蘭籍的女傭博耶娜卻向克里斯托瓦暗示其實是被馬爾庫斯下要害死好模奪財產.於是半信半疑的克里斯托瓦開始了他的鄰居接觸,確認韋伯耶娜可能故意說他前雇主的壞話,因為馬俺庫斯看來極為頹喪厭倦了斯德哥爾摩的生活.有一天當克里斯托瓦又跟蹤妻子時,發現她進了一幢湖邊別墅,原本他打算入內抓姦,卻不料發現妻子正與一個白人男子打鬥,他上前協助妻子卻失手殺死了這個俄羅斯人.兩人慌張逃離現場,卻在進入家門前遇到了馬爾庫斯,讓他看到了一些他們從殺人現場帶走想湮滅的物品.於是克里斯托瓦很擔心當案情為大眾所知曉時,馬爾庫斯會想起今天他所看到的場景進而去檢舉他們.於是他試著想要抓住馬爾庫斯殺妻的證據想藉此來勒索他做條件交換.事實上克里斯托瓦夫妻都是智利人,他們是因為政治因素不得不離開家鄉到歐洲生活,所以在瑞典克里斯托瓦藉著寫作偵探小說為生,他當下正在創作的正是一本以他自己當前生活為本的小說,因此他已經將對妻子外遇的懷疑,對鄰居殺妻的可疑,與自己在湖邊別墅中所發生的事情,與自己心中的盤算都當成小說人物與情節寫盡自己的小說中,但是湖邊殺人事件後,他意識到自己的小說不能夠再按實際的情況來寫,否則將來人們查到小說,不就知道他是兇手,於是他開始半真半虛的繼續他的寫作.不久後女傭博耶娜在家中遇害,負責調查的警官董甘找上了克里斯托瓦.董甘透露博耶娜的死可能與俄國的黑手黨有關,但是克里斯托瓦卻以為是馬爾庫斯為了害怕自己殺妻的事洩漏而做掉了博耶娜.加上為了讓馬爾庫斯不透漏他曾看到的事情,他故意引導董甘可能其他人殺死博耶娜.於是他向董甘陳述這些從博耶娜聽來的謠言,於此同時,馬爾里斯看到了在商場商議事情的克里斯托瓦與董甘,以為克里斯托瓦是向董甘檢舉他殺人,他趁此時潛入克里斯托瓦家將他沒有及時丟掉滅證的殺人證物偷走.於是當克里斯托瓦回家時,馬爾庫斯拿著證據要脅克里斯托瓦.後來雙方達成默契,馬爾庫斯先是搬離,後來可能移居到他最喜歡的古巴去.而克里斯托瓦夫妻則因為外遇的還移而離婚分手,可里斯托瓦移居葡萄牙,馬賽拉則曾此不知所蹤,幾年後,董甘去葡萄牙度假,帶了一本朋友電腦上印下來的小說,要在這次旅行中讀它.卻在路上遇上了克里斯托瓦,原來那便電腦是克里斯托瓦離開斯德哥爾摩時寫作用的,不巧卻賣給了董甘的朋友,朋友一看小說中有提到董甘,就把小說印出來給他.克里斯妥瓦知道後,在董甘離去後,開槍打進自己的喉嚨,死了,而董甘知道他突然自殺死亡,回去翻看小說,才發現那是一本牽涉到三條命案的自白書.
救我的看法上,這並非是一本單純的偵探小說.從主人公對真實與虛幻的混沌不清的角度來看它,似乎有那麼點意思.但我以為這種真實與虛幻不清是源於另一個面向.讀這本首先讓我注意到這小說的人物,這些人物其實具有內在的共通性,這共通性就能連結出一種完全不一樣的觀點,殺事件發生的地點明明是斯德哥爾摩,但是所有的人物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那就是他們全都是政治烏托邦破滅後的失意人.馬賽拉的父親曾是智利獨裁者皮諾契特下的高官,權威專制統治稱霸政壇,但皮諾契特下台後,這些曾經風光的人,並沒有完全受到懲罰或流亡,有部分甚至還能在智利國內利用政商關係撈錢,但是馬賽拉卻痛恨這種生活,因為讓別人以為他是靠姓氏為生令他痛苦,因此與其在國內遭人唾棄,不如離開,轉到歐洲生活.克里斯托瓦的父兄一樣曾在皮諾契特的政權統治下受益,但他個人卻心儀社會主義,於是當新自由主義成為智利新政權的主軸價值後,他的不削自然轉為離開母國,也到歐洲生活.而女傭博耶娜原是波蘭大學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生,卻跑到瑞典幫傭,因為彼時波蘭共產黨早已受唾下台,馬克思那套主張被棄如敝屣,一個研究生只能淪落他國幫傭,心裡的不忿可想而知,那位被殺的俄國人實際原是蘇聯KGB的人,卻因為蘇聯解體,KGB政治地位衰退不得不到瑞典買賣藝術品為生轉售國內為生.至於董甘探長,其實他也是智利人,甚至他比克里斯托瓦還更具老資格,他是皮諾契特之前的阿葉德政府的官員,是一位篤信左派共黨信條的人,阿葉德被推翻後,他就來了智利,至於馬爾庫斯雖不是拉美人,卻是一位嚮往古巴與南美左派生活,崇敬卡斯楚的歐洲人.從這些人物各類背景,各存不同的思想的烏托邦,在這種條件下生活在單調冰冷,秩序,與民主的瑞典斯德哥爾摩簡直大異其趣.這就讓我聯想這是一個關於政治失意者或流亡者的題材.
在這樣的故事中,表現的是政治失意者或流亡者在打發無邊無際單調的北歐異國生活與他們原有的思想,價值間落差間所產生的虛幻衝突,這樣的流亡或逃離生活與過去經歷拉美政治風雲的起伏相較,形成了三重空間,這三重空間分別是現實中的流亡地,流亡前的母國,以及目前由政敵統治中的母國三塊.這種混合著自己的想像與對自己越來越陌生的母國的差異形成了現實與想像的落差.在現實中的流亡地,斯德哥爾摩,寒冷單調冰封是他們面對環境的真實寫照,但更是這些小說人物對現實的感覺寫照,以致產生悲觀主義,失敗主義,挫敗情緒,冷漠情緒,懷疑,心灰意冷和不適應感等失落.隨著時間的經過越發的加重了對自身懷疑..而這三重空間有時是以單一空間的形式出現,更多的時候是兩重甚至三重空間,是由回憶構成交替融合的是對記憶的重組.這裡很好玩的是,由這些角色在流亡國的言行逤產生的另類諷刺,買賽拉雖然不削於他的父親過往的權勢所擁有的特權,可是在斯德哥爾摩,表面上她是個演員,實際上卻是靠著父親暗中接濟,利用他提供的金錢在瑞典販賣假畫,其實並沒有外在表面的光明,克里斯托瓦到了歐洲後,很快就放棄了他的左派烏托邦思想,而博耶娜與俄國藝品收購商都是對原共黨烏托邦思想與社會崩解後的嘲諷,至於董甘這位智利前共黨員,不但是逃到瑞典,甚至他完全改為信奉經濟民主的北歐體制,還成了體制下的警官,尤其他在商場上喝著海鮮湯享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陶醉的景象更是對原有信仰形成強烈諷刺,表面上這些人似乎都脫離了原來的烏托邦思維或國度,但實際上,在這小說裡,你常看不到他們屬於瑞典人行為心理的一面,從交友的範圍,到語言使用,甚至日常看的節目,聽的廣播,都依舊是南美提供的資訊,或當地移民族群所設的媒體,可以說他們簡直是身體活在瑞典但內裡卻仍在活在母國的奇異組合體.
事實上這樣的移民出走母國者有三種不同的可能結果.第一種是一直無法與移居地社會同化.第二種雖已融入移居地社會,卻擺脫不了鄉土文化的根.第三類政治移入者融入了移居國的社會,並從母國的土壤中拔出了根.因政治因素出走或流亡者大多是在成年以後才移居國外的.而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童年的記憶和教養是最深刻的,不可轉化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每個人實際上都生活在他或她的前半生中.但流亡者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成為一個精神無家可歸的浪子.一位移民要遭受多重分裂與挑戰,他失去了他原有的地方,他進入一種陌生語言,他發現自己處身於社會行為和準則與他自身不同.於是他感到了自由後的失重,產生了認同危機,最重要的是政治失意者不是主動的移民者,而是被動者,以致除了以上這些個多了一份小心翼翼的謹慎與約束,這形成了更大的壓力與問題.
因此回到一般意義上看這部的偵探小說,克里斯托瓦究竟是否是真的兇手,或殺人,其實是不得而知的.因為,留在電腦硬碟中的書稿還是自白,其實不情楚,在虛實不明之間,克里斯托瓦都知道不能將全部的真實寫下來,必須真實與虛幻參半,而最後的自殺與其是說逃避警方的追捕,還不如說他已經都不清楚自己究竟是誰?又是怎麼會到了葡萄牙的渡假地,不能找到自己.那結局當然是如此.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