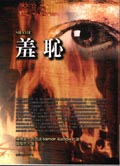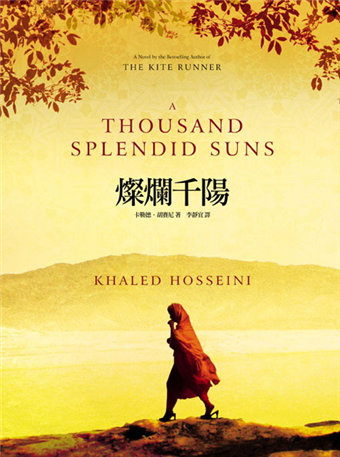布赫迪厄論電視(Sur la television,Pierre Bourdeu)
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eu)是法國的社會學者.原來是想看他的另一本作品"區隔: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La Distinction)",它被評為20世紀最重要的十部社會學作品之一.但居然意外的發現,這本書根本沒有中文版,兩岸都沒有選擇出版.所以轉而找了這本由布赫迪厄電視演講轉譯成文字的作品.以電視演講的方式來批判電視文化是本書的焦點與結構,但是以電視演講播出批判電視機制的傷害與問題也算奇葩了.
書的論點如簡化成電視媒體機制的強力發展已經產生對於其他文化領域包括藝術,科學,文學,法律,哲學等的危險恐怕不決對恰當,畢竟他說布赫迪厄花了大篇幅還是著重在其間的邏輯與因果對應,而不是一個簡單的結論.但簡單正是電視媒體機制的特性與缺點,也是作者抨擊的主要切入點,所以就電視演說而言,沒有我簡化結論的說法,觀眾恐怕會被枯燥與來不及反應的推斷論述給弄睡了.這正是奇葩的地方也是作者試圖以電視對抗電視的原因吧.
書的內容以出版來說不多,共兩章,其一是講述電視製作錄影場與幕後購過技術面機制所帶來的影響,其二是上述可視物件與人物以外其他相關的無形結構對電視與其他文化領域所產生的影響與效果.做為一種新型態的大眾媒體,電視所產製的內容有些特性與報紙不同.因為時間有限與面對大眾對象的特性.它所產生的或樂於產生的是公共汽車式的內容,就是任何一個人沒有需要太多額外條件便能上車,便能理解,不需要過度過多的專業智識與學習.所以它一面產製這種平庸不須過度思考,或只能在簡單快速思考,或毫無意識思考下通過人腦的東西,它一方面也要注意內容的平和無衝突性.但是為了搶佔收視率,在這些平凡平庸平和的內容上,又希望能夠創造戲劇性,或某些訊息之外的獨特性,所以即使是最嚴肅性領域範圍的東西都要轉變成讓人能簡單理解,具有最大的娛樂吸引或戲劇性效果,還要能搶在其他同業之前獨特,獨家性..或是主張一種絕對神奇的道德主義與規範,讓主持人或播報人成為心靈小導師,塑造出典型的小布爾喬亞道德代言人,來引導出人們尊從他們提出的對於社會問題應該如何思考的一種市場連結與價值,而以上這些特性便是電視媒體的經營者與錄影現場技術型的工作者最基礎遵從的電視機制規範.
而主要控制著電視內容特定的關鍵要素除了以上的因素外,還包括了在這些以上的外在結構.主要是錄影現場外的整個電視媒體在社會所在的位置與它的影響.當它所在的地位逐步推高,它的影響越大,那麼爭奪行業的排前絕對是電視媒體經營者的主要任務.換成白話的說法,就是追逐高收視率,與它帶來經濟力與社會影響力.因此構成最大市場份額的方式訪就如選舉一般,就是力求大眾化,通俗化,媚俗平庸,排除深思轉就快思甚至無意識.如果便能擴張該媒體的"權力場域".權力場域是這本書後半部主要論點,當高收視率高影響力出現,電視媒體的權力場域擴張到前所未有的地位.而這種擴張可不單單是這種形體的變化,它還改變了其他文化生產所原有的權力場域.,比如為了論歷史或財經問題,電視的工作人員可能不選擇與該領域的專精或頂尖者合作,而選擇能以最簡單的大眾語言解使某種專業問題解答的人,但這樣的人往往在他的專業權力領域只是個半吊子,或是專業邊緣人,但是透過電視媒體權力領域的影響,久而久之便能改變這樣人在該專業權力領域中的位置,而這單單只是為電視台喜歡找他,非專業領域的觀眾喜歡他的簡明,但往往這樣的人在專業上卻得不到同業的認可與尊重.不過權力場域改變了他的地位愈名譽,在本書中布赫迪厄舉出了許多名字來說明這現象,比如同樣是法國的社會學者阿宏(Raymond Aaron),作者以為他就是當上了媒體的主筆才有了名聲,而能夠經常的以社會學者的身分出現,但他的學術成績卻讓布赫迪厄不以為然.
作者在此提出了這種權力場域改變可能所產生的一種效果:季諾夫定律,當一位文化生產者越是自主,特殊資產豐厚,而且注重封閉市場,其中只有競爭者是客戶,那他就傾向於抵抗,相反的,他越是把品定位於大量產製市場,他就越傾向於和外在權力合作.也就是與國家,教會,政黨,或是今天的新聞與電視合作,並臣服於它們的要求與命令.從社會現象簡單轉成白話來說,比如電影,文學作品,音樂演出,舞台劇目或是關於傳統建築,飲食,服飾等文化生產者越是靠著自立在自己的領域活躍,他就比較可能迪利在以上所說的國家,媒體,,教會,政黨權力場域的控制.反之,它就只能搖尾乞憐.,因此,收視率高低決定了個別電視聘到的權力場域,也相對定義了在期間工作人員的權力場域,以至於一個根本與科學,哲學,歷史,戲劇等文化生者無關的電視記者或電子媒體工作者能夠決定了其他人名聲,知名度,或是它的存在與否,自然就產生了無知,無意識,低端,反智,不專業卻去引領專業的權力領域,與它的發展範圍與結果,前述的阿宏或是本地上到太空下到子宮無所不談的名嘴現象便是它實際呈現出現的案例,而這便是這本說所說的電視機制獨大下對於其他生產文化領域所產生的傷害並使其陷入危機的因素.
對於季諾夫定律在電視機制力量呈現它影響其他文化生產者的現象,布赫迪厄提出要提高文化生產者的進場代價並加強出場的責任.這樣就能讓失敗者不至於藉由外在結構的權力場域來改變專業的力量.個人雖然不表反對,卻以為這其實沒有太多用處.因為現實生活裡電視機制權力場域的影響確實如這場1996年電視演講所表達的憂慮是完全一致的,更甚者,網路的普及,分眾化越細,這種季諾夫效應就更加明顯.連政治人物都得要買網紅的帳,在鏡頭前面前唯唯諾諾只因為權力場域的改變能帶來選票.所以說布赫迪厄的說法絕對不是學術工作的文字遊戲,它是實在已被時間與現實給證明了.令人不得不佩服,而或有人會提出布赫迪厄迪於電視機制產生低下平庸反智的內容與現象的批評是一種菁英主義批判大眾主義,菁英文化看不上庶民文化,這可能算事實,卻也不能單純當單一事實來看,畢竟全場域的掌握與改變確實決定了文化生產者的地位與經濟性也連帶著破畫了專業者的生存空間,而這是布赫迪迪厄這種社會學者不能忍受的,相對的也更令人好奇他的"區隔: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內容究竟是什麼.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