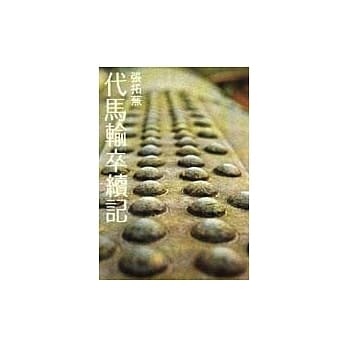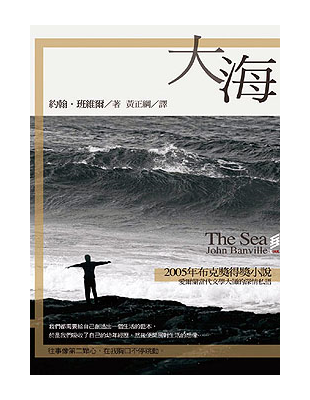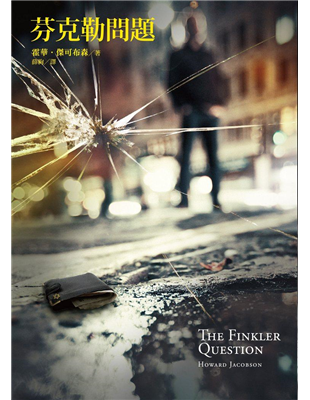
芬克勒問題(The Finkler Question,Howard Jacobson)
芬克勒問題.芬克勒是這本小說中三個好友主角的其中一人,他是猶太人,芬克勒問題可以說是猶太人問題,但芬克勒自己強烈反對猶太復國主義,反對以色列屯墾巴勒斯坦,所以芬克勒問題又成了反猶太人問題,一個猶太人卻主張反猶太人,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那又繞回到"猶太人問題"上了,不過,個人觀點裡這小說最終寫的其實就是人的問題,只是以猶太人來表示而已..
以上說法看似矛盾,其實並不.個人回想我們過往看過的關於猶太人的影視,文學,歷史作品中,基本上都透露出,或創造出一個顯明的形象,可能是受迫害的,悲慘的,容忍的,也可能是虔信,宗教的,或是新聞裡自立戰鬥,軍事對抗的,還是全球化下新科技新創企業的,也可以是恰好聽過一些小提琴大家,克萊斯勒,海飛茲,梅紐因,哈西德,帕爾曼,祖克曼等專技藝術者,或是那種很會賺錢懂得積累財富的富豪.但實際上,我們其實好像並不真的了解猶太人,因為以上所呈現的都是影響力的,正面的,值得同情讚許的,但關於他,這個人,他們,這群人的真面目,因為這些作品或成績創造出一個我對他或對他們的的刻板印象掩蓋了這些真面目,而且常常以他們去取代"他'做為代表.於是我就會以為我們懂得這個問題.是以常以為猶太人問題是集體的種族問題來寫下論點,其實這裡也有他的個體問題,非關種族而關於個人的部分,芬克勒問題就是以此體寫出的作品.
小說的主角是三個住在倫敦的鰥夫,李柏,芬克勒,崔斯樂夫.李柏曾是芬克勒與崔斯樂夫的中學老師.此後三人維持了數十年的交情.說三人是鰥夫並不精確,真正亡妻的李柏與芬克勒,這兩人恰好是猶太人,崔斯樂夫是一個興趣廣泛但實際上對各項卻只有零星片段理解的組件式人物,他不是猶太人,他沒有喪妻,而是歷來對感情太隨便放縱,他有兩個兒子,兩個兒子個媽媽是不同人,與他都沒結過婚,小孩都是由女方養大,崔斯樂夫在情感生活上應該是完全缺乏專一性與真實性的另類鰥夫,是一個在情感上,工作上都過著半調生活的英國人.三人的共同點就是在藝文藝術領域.李柏雖是中學教師,但曾擔任過影劇記者,認識許多明星,知曉八卦,寫了明星傳記致富.芬克勒則擅長哲學,以哲學為題寫的許多暢銷書,還上電視講解哲學,是三人中的名人.崔斯樂夫則在BBC製作深夜藝文節目.所謂的故事是由崔斯樂夫有天晚上在街上路過他兒時經常駐足櫥窗外的樂器店門前遭到一個人搶劫並毆打,崔斯樂夫沒看清打他的人是誰,只聽到搶嫌臨走時留下一句話,似乎是"你朱",事後他推敲了半天這句話的意思,懷疑對方以為自己是猶太人,所以才動手行搶毆打自己,畢竟在歐洲有許多恨猶太人的人.而隨著疑慮的加重,崔斯樂夫居然開始認為自己一定與猶太人有某種關聯,甚至自己應該就是猶太人,在於芬克勒,李柏討論無果後,他開始過起了一種新生活,就是假裝自己是一個猶太人,從外表學習猶太人的裝束,到學習希伯來經典,猶太教傳統ˋ,甚至他還與李柏的姪女,一個女猶太人成了情侶.整本小說就是在寫這個崔斯樂夫如何模仿假裝自己是一個猶太人的過程.相對比之下,兩個真正的猶太人因為喪妻,都正在經歷著他們喪妻後的新生活.形成了兩個真的鰥夫與一個假的鰥夫,兩個真的猶太人對一個假裝自己是猶太人的生活對比.
所以如果想從中看到曲折離奇的情節,或是感人肺腑的故事,或是所謂的故事,基本上這本小說沒有.他是心理活動,思維呈現為主的小說.李柏作為一個父執輩,一個老猶太人,小說確實藉著它來呈現出傳統老猶太人的情感,言行,傳統,思想,他對亡妻的愛與思念,他對於情感的專注珍重,即使他曾有機會在一幫有名的女明星中穿梭並博得他們的信任好感,他也未曾藉此踰矩,娶了一個傳統猶太人瑪兒琪為妻,雖然曾遭岳家嫌棄貧窮,但經過李柏努力,不但事業尚可,並與瑪兒琪度過漫長的歲月未曾出軌,相比之下芬克勒雖是一個猶太菁英,有名,但他卻加入並組織了反猶太人的組織,他順應潮流,視以色列的復國,或是在巴勒斯坦屯墾區的做的事,如槍擊或屠殺被懷疑可能威脅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的行為表示不齒,覺得這些行為跟納粹滅族屠殺的行為並無二致,所以他的組織都是一些"愧猶"這來參加,愧猶意思是"愧疚或慚愧的猶太人"的意思.他的老婆黛勒雖不是猶太人,卻反比他更熱衷於學習猶太傳統,甚至照傳統皈依猶太教受洗後才與他成婚,但是芬克勒對此並不感興趣,他是一個反對猶太人的猶太人,也是一個經常遊走在出軌召妓邊緣的男人.至於崔斯樂夫他與李柏的姪女荷芙琪芭成了情侶同居,還藉由這個身分進入了李柏他們這個大家族的生活裡,主要是藉著這位英國人參與李柏家族活動,學習猶太宗教儀式,協助荷芙琪芭準備創設英猶紀念館,透過這些來顯出一個假裝的猶太人如何體現出或觀察出真正的猶太人該是怎樣的.
李柏因為聽到一個老友的孫子被反猶恐怖份子給炸瞎了眼睛,又知道了崔斯樂夫曾與戴勒出軌偷情,加上對亡妻的思念種種重壓,最後一個人坐車到曾與瑪兒琪共遊的海邊跳海自殺,而芬克勒得到噩耗又讀到了黛樂留下的私信,信中她斥責芬克勒雖是一個愧猶,但實際上他無時不刻不想以一個猶太人的身分行事,他的愧猶是因為他害怕猶太人好不容易取得一點復國成果,找到了塊地方,會因為過度的主張而丟掉全部,他才知道這個他不以意的妻子,竟然從另一個角度開啟了他對猶太人身分的另一個哲學面想思考.至於崔斯樂夫則因為一場公園拯救小孩的糾紛裡,意識到為了一個被懷疑的猶太身分而死固然荒謬,但是為了一個虛擬的猶太身分而活也同樣不值得,因而悟出了自己與荷芙琪芭情感上的差距與隔閡,誰也不是誰的命運與責任,這一切在李柏的葬禮上被他們各自領會,芬克勒可能會坐回那個猶太人,而崔斯樂夫又回到他那個拼裝式的生活.
作者的手法看似不明顯,對比的說法是我個人推敲出來的,用對比來顯出差異,好玩,與荒謬,是以我以為這小說的目的也不在於猶太問題或反猶太問題,他就是一個人的問題,身分,種族,信仰,價值觀,刻板印象在在阻礙或導引了生活裡的一些細節走向,它可以是疏通交流的管線,也可能成為阻礙彼此情感的高牆,小說的基調是有趣,幽默,好玩,但背景後面是沉重,憂鬱與傷痛的,只是故事性不強,對一般人而言太拖沓,也少了爆炸性,加上對許多猶太習俗或意第緒語的困惑不解,可能會讓人讀不懂.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