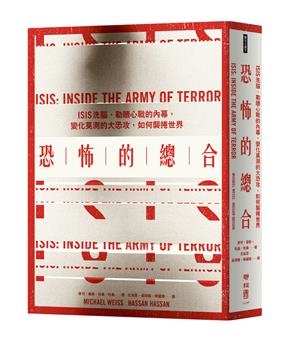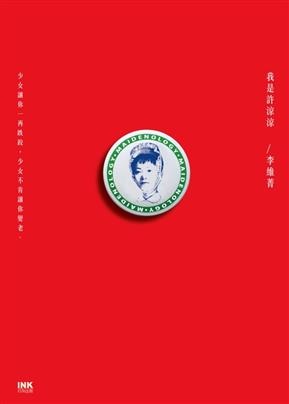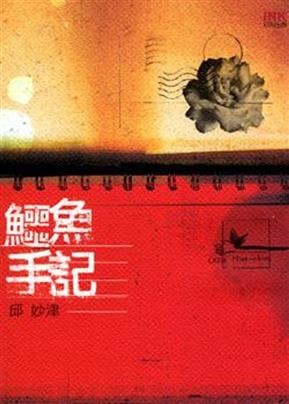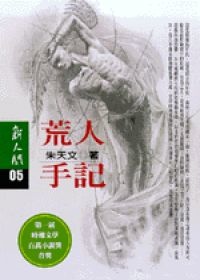
荒人手記(朱天文)
"看什麼書?"."哦...小說...荒人手記!"."作者是誰?"."嗯..朱天....文".旁邊的人看我讀這本,有了這樣對話.但是,如果他沒問,我一直以為作者是朱天心,直到回答問話隨手翻到書的封面,才發現弄錯作者到此刻,雖然他們是姊妹,但終究是不同人.不同在這裡挺重要的.手記共15篇,份量都不多,但是內容卻不易理解,這並不是因為作者用了甚麼難懂的結構,或是特別手法,而是太多不明白的比擬敘事,這些比擬包括使用一些電影作品裡的橋段,對話,導演的影像敘述意義,關於色彩學分類用詞,關於繪畫,雕塑的藝評,關於佛教與其他宗教理用語,或是關於傅柯,李維史陀的主張與作品意涵,如果原來就不懂這些,當然就不可能理解以這些做為比擬手法所想表達的意思,而這是閱讀本書的難點,即使路人我恰好前段時間看過一點傅柯,李維史陀,也未必有把握理解作者某些地方的意思.
手記是一名叫小韶的男同志,在他染上愛滋病的朋友阿堯的死亡後以此出發回顧他的同志生涯,阿堯是他的"性"啟發者也是自幼玩大的朋友.在這些手記裡顯示著小韶的同志生涯充滿孤獨,游離,無根性,彷彿是活在主流社會外的一個異類,一個活到四十歲的社會邊緣荒人,所以書名叫做荒人手記.雖然小韶是名男同志,他也進行著男同志該有的行為,但是本書從頭到底,小韶其實一路都試圖找尋自己在異性戀社會裡符合主流社會價值的位置,一個兒子,一個男人,一個哥哥,所以他一路其實是質疑著自己的行為卻又不得不進行被啟發的意識,因此而膠著與痛苦,小說裡共有8個與他有關係的男同志,其中主要的是阿堯,初戀的傑,與當前已共同度過七年的伴侶永桔,其他則是一夜情或是不知名的野餐偷吃對象..
最近對岸的央視正發起封殺"娘炮"男藝人.首先引發的問題是甚麼外型表徵與舉措會被稱為"娘炮"?誰又符合這種條件?誰來認定?但有一個問題卻沒有被列入疑問的前提,那就是為什麼要封殺娘炮?通述的理由是娘炮會誤國,至於如何誤國,不是說不出理由,便是以缺乏男子漢風易淪為東亞病夫等可笑的理由.其實真正誤國的正是這些腦子未開化的迂腐論點.為何人不反對女漢子卻反對陰柔男性,背後真正的原因是娘炮引發了陽剛氣男藝人的恐慌,一位娘炮小鮮肉被人為沒演技沒技能,但演出一部電影拿走一億酬勞,而那些陽剛男藝人只有他收入的十分之一,沒辦法娘炮鮮肉有人看有市場.這可不得了,輩分高陽剛演技好輸給了娘炮資淺演技生澀.這不但大大挑戰了既有的價值,也挑戰了權力結構,決定權力的方式不同選擇也就不同了.套句通俗電影的台詞"黎明不是張國榮",梅蘭芳也不是程蝶衣,他們都演坤旦藝人,這是導演挑人的結果.胡軍,梁家仁可以扮演丐幫蕭峰,但曾幾何時連鍾漢良都能演蕭峰了,而這就是權力的作用,製作者的權力能決定電視劇裡的蕭峰該是怎樣的.而同性戀觀念的興起引起權力的改變在這裡扮演兩種狀態,一種狀態在前面提到傅柯與李維史陀裡,就是小說內文被編號為5的那篇,另外一種角色則是這本內容佔據了大半的女性陰柔權力的提升,權力的作用是gay沒有queer正確,而幾年以後又將讓位給LGBT.
男同志小韶孤獨又苦悶的反覆自我探尋,既想融入這個異色世界卻又不能不理睬他自身的性語言,這兩種不同的境地的穿梭著,以小堯的死亡帶給他對於同性戀者存在或生活意義的糾結.而李維史陀在這裡獲得了小韶的認同,傅柯則沒有,原因不是因為他贊同,而是他以為他反抗不了."李維史陀終其一生追尋的黃金結構,我心嚮往之,以為它也許只純在於人類集體的夢中".在這裡作者以李維史陀代表的是一種既定的秩序,結構.每個人,每件事,每種出相都有一個他存在於世間既定的位置,有他一定的順序列隊,而血緣,繼嗣,姻親所形成的關係網路是人類區別於自然,屬於人類社會所特有的東西,動物無從區別自己與自然的界線,所以他還沒有從自然脫開來,關係網路於是成了可與自然匹敵的獨立體,與自然繼對立又統一,而李維史陀終其一生就是叫找出暗藏糾結的結構.而小韶的疑問是同志究竟在人類裡的位階是甚麼?它的產生是源於自然?抑或是人類社會特有的?在關係網路上的位置是?在李維史陀調查的巴西原民裡,崇敬祖先的觀念與照應活著的人同樣重要,他們不承認吳子女之人具正式的社會資格,因為得不到後代崇拜的人就不可能擠身於祖先之列.所以孤兒,單身漢都被部落歸類為殘疾人.而同性戀剛好就是當然的失掉了他在血緣,姻親,繼嗣裡的延續作用,所以依照李維史陀的追尋的結構裡,哪可能找到一個合乎於他的位置,除了排除在部落集體認同之外以孤獨,殘疾,邪惡的身分存在著,旦柚並不真的被視為存在.但是傅柯就不一樣.在那個認為同性戀邪靈是源於親屬父母的壓力,屬於自己的一部分的社會,他提出性與權力的關係.大多數的人都活在聯姻機制中,多生育,亂倫禁忌表面上性議題進入了現代後脫離了宗教,道德倫理的制約與束縛,但實際上是新的控制不靠權柄,而轉談技術,不靠禁律,靠讓它看來正常化,不靠懲罰,靠管理,而肉體成為知識,知識成了一種權力,而性與權力的關係就從單純的從屬包裝成複雜多樣的機制,但實際上的本體仍是一樣不變.相反的,性成了公共事務,越來越擴展到事務與肉體外面.表面上看來是如此開明,對於某些被認為違反自然的事情,它用中立的語彙或是科學性的包裝,假裝社會已經能夠容忍,接受,實際上只是採用了更精緻的訓導與調節,看似給予自治權,但實際上仍是掌控,仍要收編.所以表面上同性戀也被新社會收編進更文明社會,表面上同性戀似乎得到允許性自主,性自由,但實際上沒有,因為那是必須在收編於權力的認同之下的,而傅柯以為這是一種假意,所以身為同性戀,傅柯不願被收編,而小韶只能考慮接受,儘管它也未必反對傅柯的觀點,但它沒有反抗的能力,而沒有那個能力也是被挾制在這個約制的結構裡,而他只能一邊苦於靈魂即身體的一元化,甚至只有身體的連結而沒有靈魂連結的伴侶關係,卻有想要正常的社會位置,是以小韶只能向李維史陀求助.
除了以上的要點,小說對於同性戀躍上了檯面後對於陰性,女性特質與權力的展現寄予著些期待,花了相當多的篇幅描寫著小韶對於這方面的認可.而對於就世界既定契約的衝擊與破壞,這裡也展現了肉體與靈魂一元化的決絕.而我以為更多的是對於現實世界的不滿與脫離,因為既不能改變自身之外的其他,也不可能完全依照自我的身體在群體之間行事,恐怕只能脫離當前結構,隱居,或苟活於暗室陰溝,而沒了致命病毒的侵擾被迫死亡,也處在上無天堂,往下是深淵的地方,那小韶在問就是那個能讓他這樣的特殊個體存在的的社會結構,關係網路在哪裡?而這也是我盡力看了這本能得到的一點心得,其他難以理解的部分,就當掠過風景吧.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