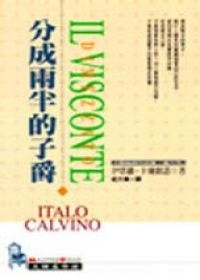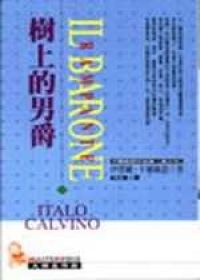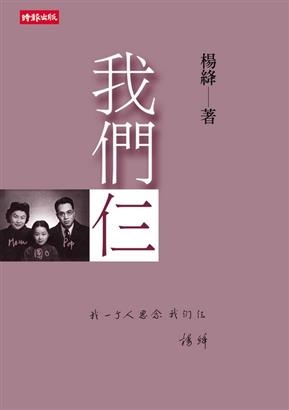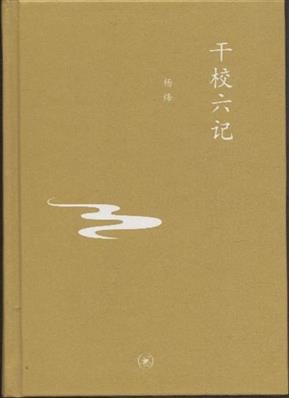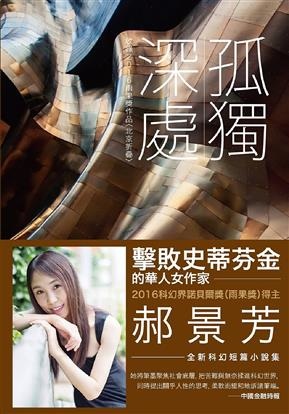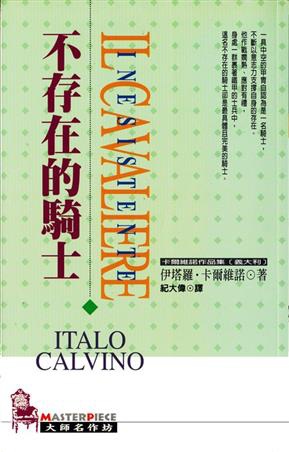
不存在的騎士(Il cavaliere inesistente,Italo Calvino)
不存在的騎士比起前兩本又進了一步,大膽的把更荒謬的人事物搬上來演出魔幻劇,敘述可以是童話但內容卻是另一個層面,這本應該是三部曲的極致.它展開對生命本質的質疑與拷問,活著就是存在?.迷惑物慾的終極或可能使人一切功能如機械般,麻木致死,那信奉心靈的最高精神就是答案嗎?也許可能不過是人文沙文主義,而那也是會殺人的,殺的就是自己,也是另一種消亡吧.
查理大帝麾下有位騎士,這騎士叫阿吉洛夫,日常的裝束與其他騎士一般,身著鎧甲頭盔護面,除了鐵甲銀白與他人不同,外在並無差異.但阿吉洛夫行事有其原則守法度,條框分明,進退有舉,具備騎士精神,貴族驕傲,與堅強的意志力.在他人眼中他是一個自我中心的怪咖,平時也不參加其他軍士間的飲酒嬉鬧,致大家都不太喜歡他,連國王也如此看他.儘管阿吉洛夫是個勇猛善戰,屢立軍功,但在他盔甲之內有個大秘密,就是阿吉洛夫並沒有真實的肉體身軀,外人看來阿吉洛夫就是一具有生命力能自主活動的空鎧甲.國王在征討途中收留了一個有趣渾人葛肚魯,這個人似乎是個沒有腦袋沒有自我的,他看到水裡的鴨,以為鴨就是自己,看到蛙也以為那是自己,不停的模仿那些生物的活動方式.他沒有思考能力到了軍營中只能接受上頭傳來的指令,好玩的是查理大帝將他派給阿吉洛夫當隨從.漢波則是另一個年輕騎士,為了報父仇進軍營.戰場上他將仇人的眼鏡給打碎了,並且知道仇人伊索哈已被自己軍隊的長茅殺死.失去了報仇的目標,他渾渾噩噩的在打鬥中見識了一位身手不凡的長春花女騎士布拉妲夢,並迷戀上她.無奈布拉妲夢喜歡的卻是阿吉洛夫.這一天查理大帝用餐,在座眾騎士無不在自誇戰功,當阿吉洛夫自傲於軍功都是扎實不可質疑不同於他人的夸夸其談.一位剛入營的青年朵利斯蒙出面反駁.原來阿吉洛夫最早能由平民升上騎士,是因為他曾救下英格蘭國王的女兒索弗洛妮亞.使她免於遭暴徒的玷污保持清白.但是朵利斯蒙卻說自己正是索洛妮亞的兒子,是索弗維妮亞與聖杯騎士所生,他能證明阿吉洛夫並沒有保持住公主清白,因此他所謂的功績並沒有自稱的高大.為了自證,阿吉洛夫提議要去找到索弗洛妮亞將他帶到國王面前說清楚.阿吉洛夫帶著葛肚魯經過千辛萬苦跨海到摩洛哥救下了索弗洛妮亞免遭阿拉伯人玷汙後,將她帶回法國安置在一個山穴裡,當阿吉洛夫帶著國王與諸騎士來山穴時.經歷過尋找聖杯騎士生父失望的蒙利朵斯正好經經過山穴,看見了美貌的索弗羅妮亞,兩人一見傾心隨即發生關係,此時阿吉洛夫與國王等人看到這一幕.於是乎想以索弗洛妮亞貞潔清白自證的阿吉洛夫崩潰了跑進了森林裡.然而事實上在此之前,索弗洛妮亞確實是長期維持著貞節,阿吉洛夫的功勳也是實實在在.漢波在尋找布拉妲夢的旅程中發現了一具銀白空鎧甲,那是阿吉洛夫的,但他已經消失無蹤,於是他穿上這具鎧甲繼續上路,並找到了布拉妲夢,那時他已經化身為阿吉洛夫,兩人發生了關係.待面具卸下後,女騎士發現他是漢波生氣的走了.葛肚魯也在尋找阿吉洛夫,卻遇上了結為夫婦的朵利斯蒙與索弗洛妮亞,他們被封為伯爵管理著展開新生活,而漢波則在一個修道院照到了布拉妲夢,此時布拉妲夢以化身為修女,正在著書寫作,寫的就是這個不存在的騎士的故事,雖然布拉妲夢迷戀著阿吉洛夫,但是成為修女的他卻對漢波有了新個感覺,於是他們可能有了個新的開始.
卡爾維諾創造了阿吉洛夫,葛肚魯,漢波這三個代表性的人物,分別代表了三種形態,阿吉洛夫代表一種精神力,意志力.葛肚魯則是單純的肉體存在,而漢波則是處在這兩種絕對極端的狀態中間.阿吉洛夫一個失去肉體只靠意志力生存的騎士,像是具堅不可摧的空氣武士,他不知道疲累,不知道飢渴,不懂得男歡女愛,雖然偶爾也為物慾或世俗事務有所動念,卻都很快可以排解.阿吉洛夫能理解生命,卻無法體會生命.與他相反的就是葛肚魯,他是一個見什麽學什麽帶點憨態的人,除了肉體存在彷彿沒有任何自我認知的精神意志力.他也不會苦惱,累了休息,餓了就吃,從不感到憂愁.雖然他有著鮮活動態滑稽的生活能力,,卻無法意識到自己的生命.漢波則是處在兩人之見的狀態.他能帶著殺父之仇入軍營,卻也能夠立即轉向追逐愛情.他存在部分的意志力與肉體共存,但是他他意至力精神力薄弱,生命脆弱,經常苦惱,為了愛情心力交瘁,與阿吉洛夫不同.而這樣一個普普通通不陷極端價值生命正是多數平凡人的寫照.
意志力精神力強大是一種理想化,而完全沒有意志,只能依賴世俗隨波而生也許理想卻是種荒謬狀態一如葛肚魯.像漢波那樣偶爾痛苦求不得或偶爾欣喜於有追求看似不理想,也多苦楚,但卻是作者認為是人類最根本的生命狀態.他以為生命就該如此.存在就是這樣,一個有煩惱痛苦悲傷快了的平凡人,如果不想像阿吉洛夫那樣不存在的活著或是像葛肚魯那般詭異,,那就大膽的進行生活擁抱生命與未來吧.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