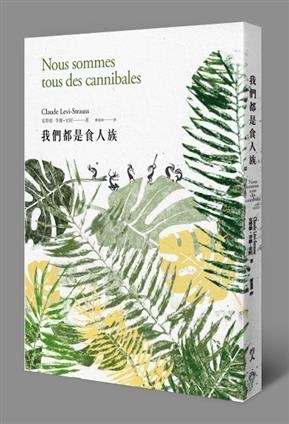責任與判斷(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Hannah Arendt)
接著兩本將主題做個提升,或以思考或觀察來看,實際都涉及思考或行動的內涵,本質上就是一種教育.在這本責任與判斷中,鄂蘭對小岩城事件有一段關於政治與教育的觀點."以未來精神教育下一代,並希望藉此改變世界,這想法自古以來就是政治烏托邦的特徵之一.這個想法的問題始終相同:只有當孩子真正與父母脫離,而在國家機構中養長,或者在學校裡被灌輸思想,使其能反抗父母,這樣才有可能成功.專制政體統治之下的狀況變是如此".此近於徐賁所寫的兒童成人化,以便於成人兒童化.灌輸兒童習得成人的價值與框架,看似提早成熟時則是限制了他們可能的異端思想,一旦獲致成功,當他們成年了,也就只會一直沿襲這種童年青少年時期被建造的思想框架,再也不能成長或改變.在鄂蘭這裡,一個人要是不能思考,就是代表不能行動.
當然事情並不是如此簡單的只針對極權國家,民主國家呢?小岩城事件的反思就是一個.美國,一個現代民主制度的代表.它沒有極權國家的集體一致性,個體可以展現自己的獨特性不必事事與他人一致.也因為這樣,鄂蘭把這個教育議題整體一分為三,一個人的身體上就同時包含了三種屬性,政治的,社會的,個人的.這樣的分法明顯是不同於極權國家將個體打碎全部屬於集體的概念,相對的,也是一種回歸人本人文思考的人的條件的根本.鄂蘭認為美國聯邦政府派軍隊進入小岩城接管學校保護黑人學生進入學校的行為是一種並沒有看清事件本質的行為,期望藉此打破種族隔離的方式也是錯的.
單看到這樣的說法會誤以為鄂蘭贊成種族隔離,支持白人學生與黑人學生分開就學.但實際上鄂蘭質疑的不是廢除種族隔離的想法而是做法,是聯邦政府的做法違背了南方州長期以來的社會習慣,也同時違背了法律,首先,他認為如果要挑戰種族隔離所顯出的不合理現況,應該從一些更具代表現的隔離現象,如保障生命,自由權等事務,最顯著的就是黑白通婚有罪的或是隔離居住或是限制黑人公民權等才是最該被先作為檢討的對象,放著主要的問題不解,卻去處理相對並不那麼緊急的事情,這種處置方式是有問題的,其次,關於高中教育在美國的法律中是屬於州政府層級的職權,聯邦政府是沒有理由以任何藉口來干預州政府的職權.其三,美國的種族隔離是一個長久以來的問題,鄂蘭認為把這種大人都不能解決的問題,推給青少年或孩童去負擔是不對的.作者以為這種做法取消了成人的權威,卻隱隱暗示了否定成人將孩子生到世界上而對世界負有的責任,也拒絕了引導孩子進入世界的義務.人們是否悲哀到已經要孩子去改變或改善世界的地步?何況,人在童年或青少年時期最容易成為從眾者,他們會本能的尋求權威引導他們進入一個對他們來說猶為陌生的世界,如果父母或老師無法承擔這個角色,孩子便會越發強烈的跟從同伴,在某種條件下同儕團體就會變成他的最高權威,結果就會出現烏合之眾或幫派式的統治.也就是民粹暴民之治.
從這裡就可以看出民主與極權本質雖不同,但一樣都有令人憂慮的狀態.而暴民問題的本質就在於個人的政治,社會,私人三個領域的價值觀點彼此扞格,導致思想紊亂不清.在政治上平等是核心.但在社會上,重點是區隔.民主國家以全民平等奠定國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以成為現代立憲政府不可剝奪的原則,平等的重要性在共和國的政治生活中大過在其他任何政府體制.但是,社會是個奇特的混合體,是介於政治與私人的混雜領域,現代社會中大多數人但半時間都生活在這個領域裡.當我門離開自己的家進入公眾世界,我門首先進入的不是以平等為基礎政治範圍,而是社會領域.為了維生或追求事業的需要,一旦進入這個領域就需要物以類聚,餐與各種組織或機構.在這裡重要的不是平等而是差異,人因差異而隸屬於某些團體,為了使團體更具可變性,她們必須和其他團體做出區隔,沒有團體的區隔,社會就不再存在.所以區隔是不可少的社會權利,如同平等是一項政治權利,問題不在於如何徹底廢除區隔,而是如何將之限制在社會領域之內,在那裏,區隔是正當的.並避免區隔的做法逾越到政治與私人領域,造成破壞.至於私人領域,既非平等性,也非區隔性,而是由獨特性所主導.我們選擇我們希望與之共同生活的人,造就個人選擇的不是一群人共同分享的同類性質,而是一個人獨樹一幟與眾不同的獨特性.但與眾不同的獨特性始終會與某些社會標準相衝突.因此社會區隔可能會牴觸私人生活領域.在這三種領域可能出現扞格時,政府必須確保社會區隔不會削減政治平等,也同樣必須保護個人在自家之內為所欲為之事的權利.
雖然小岩城事件的反思看似不是這本書的主要部分,但個人以為作者在此的探索提供了一個思考的根本.責任與判斷!本書所談的可能是個人責任或集體責任,而是否有責任正是從個人的這三個成分去探索去判斷.是以雖然書是從艾希曼的審判談獨裁統治下的個人責任問題,實際上討論的正是政治面的.在審判過程中,艾希曼主張自己只是大機器中的小齒輪,一切的作為都只是依法行政奉命行事而已.事實上,抱持這想法的不只艾希曼,在耶路薩冷的審判與更多年後的法蘭克福審判上,整個德國都大多數人都是這樣的想法,按這種思維,納粹統治下德國所有人都只是邪惡殺人機器中的小齒輪,並沒有人真的造就了悲劇,他們都只是依法奉命行事而已,因此都無罪責.但鄂蘭認為討論罪責就要從行為者個人層面上來討論,不能隨意以小齒輪逃避.因為政治不是兒戲,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支持並執行屠殺猶太人命令就表示拒絕與猶太人與其他民族共享世界,既然如此,鄂蘭認為全人類中將沒有任何一個成員,願意和你分享這個世界,這就是艾希曼必須被處死的理由.鄂蘭認為高舉倫理法則本身並不能完全阻止罪惡.其實真正造就人們不敢為惡的是一地的風俗習慣或習俗,而這些風俗可經由人為而改變.納粹政權下最可怕的並不是他們用暴力脅迫人民支持,而是將政治體制翻轉,使得人們原本習於服從的法則產生質變.不加思索的服從當局的規定與指令,並且以服從為理由迴避了執行命令當中的思考,把一切都交給規定與領袖說了算,沉淪其中而不自拔,這才是真正的罪惡源頭.
鄂蘭認為被動享受知識不等於思考本身.思考是一種對話,與自我對話.而這個關於思考的推論則從蘇格拉底說起.蘇格拉底用自己的生命帶來表示一個觀點,那就是"寧受不義而不為惡".對蘇格拉底相信"我"並非完全孤立的存在,而是一個"二合一"的自我.這個"自我"始終與"我"相伴.如果我們的行動或意見與他人產生矛盾,我們雖可以遠離或是離開,但卻無法逃開"自我",這個自我是我自身的夥伴與見證者,我們固然可以暫時無視於它,投身於其他各種事務中,但終究無法完全與之分離. 對蘇格拉底來說這股思索的動力出自於與自身相伴的自我,這個自我不斷與我進行對話與交流,我們不可能逃避它的存在.既然寧與世人不和,也不願與自身傾軋.那麼在考量是否服膺或追隨他人意見前,我們最該做的是與自我一致而不矛盾.如果產生自我產生矛盾豈不就像招來一個無所不在的仇敵,如果必須一直與這樣的矛盾相處絕對不是愉快的.他認為人們應該自問是否願意讓我們那種為惡的"我"與"自我"常相伴隨.鄂蘭相這樣的自我可以讓人從真實世界中抽身而出開始反思,這樣的力量或許只是種消極不為,使人不再投身惡行,但在原有倫理法則與律法都不再能遏止人們服從命令之時,透過這種方式至少能使自己不隨波逐流地做出那些不堪的惡行與災難.
作者試圖援引康德的觀點來建立判斷的基礎,康德發現每一個人都擁有蘊藏在自我之中的道德法則.道德命題其實對於人來說,是自明的,問題是你願不願意去正視它們.鄂蘭以為這是在尼采宣布上帝已死之後,對於道德世界的重建.康德認為道德行為首先建基於人與他自己的交流.他指出有兩樣東西,我們越是經常持久的對之思索,它們就越是使內心充滿常新而日增的景仰和敬畏,"頭上的星空與我心中的道德律".道德律讓處於廣袤星空下的自我重新找到了位置,找到做為一個人的尊嚴.康德的思想中道德行為與外部的法律是毫無相關的.真正的立法者是自我,而且這個自我並不需要科學,也不需要哲學,這是最普通的人均能力所能及的.然而自我發出的理性聲音,可能會遭到拒絕.這個拒絕的環節就發生在人的意志這一部分.人的意志可能被感性的愛好或誘惑所引導,而不追隨理性,從而陷入道德謬誤中.處在這一情況中的人,等待他的是良知的審判帶來的自我鄙視.而判斷個別事物的能立不同於思考能力.思考活動處理不可見者,處理不在場事物的表象,判斷活動則關注個體和近在眼前的事物.這蘊含著兩件事.一方面,我們對於道德的判斷並非援引普遍法則而做出,我們可能面對的是一個典範事物,並直接從中感知並做判斷.當然,典範或許不完全可以放諸四海或萬世不變,它可能會有文化上或時間上的特殊性,但它確實可與他人共享,因為我們與這些人亦共享了同樣的感覺.因此,當我做出一個道德判斷時,我並非完全地陳述個人感受而已.當我對人們做出這項宣稱,要與人溝通時,我勢必是想像著,在人們與我共享的這般感覺之下,有可能亦會認可我的判斷.透過想像的過程,將自己的宣稱予以擴展試圖將他人的感受與想法納入其中,使自身判斷的有效性進而擴展,而形成一擴展的心靈.當這個想像能考慮與觸及到越多人的處境與狀態,就越能增強我的判斷所具有的代表性,如此我的判斷不再只是純然的一己之思,而是盡可能地將各種可能都納入其中,克服了原本自我本位的狹隘性.對於鄂蘭來說,這樣的道德判斷帶來了突破的可能性,如果我們能將這樣的思路到道德與政治判斷中,那麼我們就可以設想一種既非法則援引亦非純然主觀斷言的是非判斷,而是主體間的相互交融,這個嘗試在鄂蘭看來是可行的.政治生活與道德判斷一樣,雖然都充滿著各式各樣的人,蘊含著人的複數性,但判斷的有效性不因此就只能建立在各種意見的隨意總和,或是利益的相互妥協.
這本書雖是幾篇文章與演講稿的集結,但基本上都圍繞在以納粹的猶太人滅絕行動與美國南方的種族隔離制度上,就個別案例上都有思想的細微處值得讓人們深思,不過也有不容易閱讀的部分,正是佔幅100多頁責任部分的道德哲學問題,從蘇格拉底引用到康德,除了猜想是原文誨澀,是翻譯的不清,最可能的原因其實是個人對康德思想與蘇格拉底對話理解能力的低落.不過鄂蘭探討極權,屠殺,還是種族隔離,水門案,教宗的惡,還是奧許維茲地下人渣的方式,確實有值得本地人深思之處.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