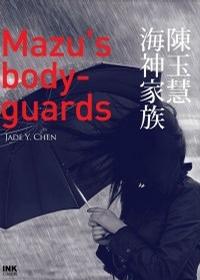
海神家族(Mazu's bodyguards,陳玉慧)
附近的店有一位老婆婆常客,他不會說國語,加上年紀大了說話聲音很小,有點自言自語的味道,所以經常發現他點餐時別人聽不懂他在說什麼.可能他注意到我常出現在那店,雖然根本不認識,他偶爾也跑來跟我說一些話,通常都是一些抱怨的家庭瑣事.前幾天,他問我當天的日期農曆幾號,我查了手機說"新曆初二,舊曆初五".隔了10分鐘,他拿了張紙又回來問日期,我在紙上寫下日期,但見他看了半天還是有點迷糊,不知是眼力不好,還是不識字,於是用筆指著紙上的字說這是新曆,那是農曆,此時他拿起我的筆,在字旁邊註記,我看他寫了兩串平假名.這才知道原來他會寫日文.老婆婆說以前是幫日本警察煮飯的,所以他能講日語,懂一點點日本字,也講了一些年輕時的事.他講出的日本時代感受與家裡老人講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樣的.倆者有差異本來就是正常的事,時代還是同一個時代,大歷史中的個人小歷史本就隨其因緣而有不同的樣貌,它不一定能反映或驗證大歷史,但可以說明某些條件下人會有怎樣的可能.
這次主題的最後一本.雖是年代最近的,但從變遷與遷移出發.所以,當時的味道依然是主角.我所謂當時的味道並不是指小說設定的人物與時代,而是這樣的作品本身出現當時的味道,比如於梨華的焰,朱天心的古都,甚至早期王藍藍與黑,都有屬於它那個時代的味道,翻成白話的說法就是某種政治正確性.以當時的味道來看海神家族此刻可能未必,但若干年後,可能如同我們今日回看嘲諷更早作品的政治觀點.
與前面幾本相較,海神家族設計性最明顯.雖是第一人稱,但小說循環於第一與第三人間,用第一人稱時,會帶上明夏的"你",時序就是當下,用第三人時,則是緩緩的道出過去的故事.小說以母系的角度來看家族三代的故事,說設計感最強指的是人物的政治設定.琉球人三和綾子來台尋夫,卻只能帶回因為霧社事件戰死的日本人吉野.來台因身體不適邂逅台人林正男,兩人靠書信往返確定了戀人關係,於是三和綾子再度來台與林正男結成夫妻,林正男曾出征南洋,經歷生死,戰爭結束後返台,因為二二八事件失蹤,其實是秘密處死.他們的大女兒靜子嫁給來台的安徽當塗人二馬,一個化名馮信文的退伍軍人,馮信文在偶然的機會下投宿在廉價的招待所而認識了一個被認為是匪諜的人因此入獄.馮信文早年在老家早有一名妻子,於是他在開放探親後獨自回到中國生活,後來因為金錢被騙只能再度回台.三和綾子曾與林正男的弟弟林秩男有情,生下了靜子的妹妹心如.林秩男因為加入台獨運動被列為黑名單而流亡巴西.基本上小說裡的男人把島內可能有的政治運動或政治事件的面向都涵蓋了,因為政治,這幾位男人都在家族生活中缺席了.而聯繫起這些的正是以第一人稱的主角.從德國回台,成年之後就逃離家庭的主角因為將與外國人明夏成婚而回台尋找親人.主角不知因為當年隨手帶走父親丟進垃圾桶由林秩男雕刻的千里眼順風耳雕像,造成靜子心如姊妹多年的仇視,因為這趟回台旅程終於揭開了真相,而藉由這趟旅程讓過往的怨恨,不解,或是苦難一一獲得化解,而得以更安其所終,流浪者回歸故土,孤獨者迎回親情,誤解者打開糾結而終告圓滿.
因為男人在家族生活中缺席了,是以這是一個女性撐起來的家族故事.其實作者的立意與取向是不錯的,但是個人認為這本小說太後設,許多的講述帶著現在的價值卻寫以前人的視角或視野,顯得設計感太明顯,反而省略了許多情感細節的發展.最明顯的就是主角的逃離,與父親的隔閡,似乎是匆匆地過場.男人的缺席要凸顯女人宿命?抑或女性的堅毅?政治的信仰不同的紛爭要讓位於宗教信仰的一致抑或寬容?男人因為各種政治理由而缺席或利益相殺,女性卻因為媽祖的信仰而聯繫,這種簡直是明示的暗喻顯然也有點薄弱.雖然書末的專訪中曾述及小說的內容有從個人家族歷史擷取,但我以為這樣的流程還是太過趨向大歷史,大社會,符合該有正向的人道觀點,政治觀點,醜陋的似乎都是由政治外加的,符合那種和諧社會的必要準則,也符合當下的正確性與周延性.是以,又回到了前一本的大哉問,難道一切都不算數了?所以這樣看與作者不同,是因為這才是真相,受害者復仇何曾忘之,既得利益者或走避或淪落或加入新起的統治者繼續維取利皆有之.顯然在經歷了痛苦期,女性也變得很政治,甚至女性都已經當上統治者,但小說還是給了一個她傳統的心靈.她只要她的愛情與家庭,其它的都是能放下的.
在小說裡的男人因為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喜好與位置,但最大的位置變化就是用千里眼與順風耳來表象,英文的書名是Mazu's bodyguards,媽祖的部將,暗指著這種男女位置的變化.然則位置的變化是否就表示思維的變化?起碼找尋一個主神的信仰標準還是不變的,神說甚麼就是標準的態度依然不辨,而不論時代是否早該演進到把定於一尊的神給拉回民間,該把統治個人歷史所定義的大歷史讓位給讓諸多個人歷史並述.從這個角度,海神家族還是可以一讀的,只是那也只是諸多個人歷史觀點中的一支,可能沒有後設所想的每一種論述或個人歷史都那麼和諧與圓滿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