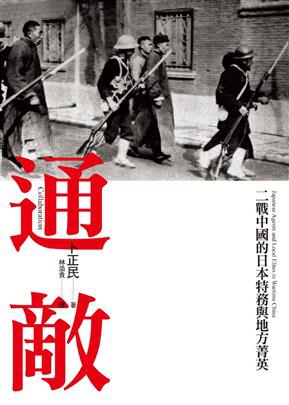山屋憶往:一個歷史學家的臨終追想(Memory Chalet,Tony Judt)
"人在哪裡,我就混哪裡!",這是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裡的台詞,從劇情中反映出來,它原帶有標籤意思,預設某種人某些場合才會說這種話.用這段台詞來表達對山屋憶往的心得,卻剛好相反.東尼賈德(Tony Judt)是來撕標籤的,因為一個人會混許多地方,有不同的角色與身份,這些身分未必是個人能左右選擇的,而Judt認為可以不必照著這些身分歷來被預設的行為準則來扮演自己,因為他自己就是這樣的,既然不限於混一地,也就沒有一個絕對純種的人,每一個人都是多種面向的混合體,與其陷於身分認同的混亂,還不如拋開身分的自我約束,在Judt的思考里,身分是一個危險的詞.
作為一個漸凍人,Judt寫完這本書三個月後就去世了.最後的時間裡連睡前都必須仔細檢查呼吸器有沒有綁正,因為已經不能自主收縮的氣管很可能會要睡夢中要了他的命,肢體已經完全不能動作更別提要如正常人一般,像未發病前的自己一樣用手寫作.不能打破漸凍人必然的行為定律,這本作品就不能出現.而以打破漸凍人狀態回溯記憶到Judt一生,他就是一個人在哪裡就混那裡的人,每一個階段關於自己的記憶都在試圖打破每一個既定角色的既有價值與模式.對Judt這個漸凍人來說,漸凍人並不單純是肢體上生理上的意義與限制,他把漸凍人當成一個比喻,一個大的集合名詞,這整本書談的與其說是個人鬆散的小回憶錄,還不如說他在試圖提出人類不要往當一個肢體外漸凍人的路途前進,不論是公共知識份子還是一般人,若因為既定身分標籤而只能必然的堅持信仰一種意識型態或某種主義,那麼將成為另一種型態的漸凍人,思想上心靈上的漸凍人,一個被禁錮的心靈.在Judt眼中世界如此寬廣,樣貌多樣,不同的空間即有相異的風情與人文,而多數人所得的結論或立場竟然如此偏狹,這不單是空間相隔所造成.
在這本回憶錄裡充滿著對於各式交通工具搭乘經驗的故事,也有作者與歐美不同國家,民族人群交流的經驗,但他並沒有藉此推崇現代化的便利帶給人們更多的見識,在Judt的描寫下,或許技術的進步能讓多數人瞬間移動到更遠更異樣的的地方,甚至可以嚐遍不同地區的食物,看到不同文化與政治體制或思想主張,擁有的比過去更多的資訊與受教機會,但是反而正是在這時刻,意識型態仍然在束縛著大眾,或各種自以為是的各式集體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且讓人們以為除那些多數人所主張的東西外別無選擇..
一個猶太人,並不認同除了血緣外大多數猶太人的習俗,宗教,乃至歷史苦難;一個研究法國歷史的史學家,並不認同大多數法國歷史學者理論性的結論,更痛恨螢幕表演式的歷史學者;一個自認的公共知識份子,看不上那些抱著意識型態各類主義的理論公共知識份子,一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信徒,仍舊偏左的行動者卻以菁英者自視.在英國出生求學,卻不認為自己是英國人,擅長法語與研究法國歷史,也不認為自己是法國人,搬去美國做了二十多年的美國人,最終來到瑞士,因為這是他最後選擇的地方,他最喜歡的瑞士山中小屋.持續的移動,持續的認可,與持續的否定,在Judt那裏這是存在與變動.編者有留下它們的原文being與become,顯然是理解這種心態的.他的觀點源於個人經驗,他從中學時期起即有三個夏天前往以色列的集體農場從事勞作,投身於猶太復國主義為這種理想奉獻自己,但最後這些經歷讓他學到的是放棄自己被賦予的信仰,成為一個普世主義社會民主人士.大學之前他已經親身體驗猶太復國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社群主義等從好奇跟隨到放棄的全過程,這些過往讓他對各種政治觀點與主義始終抱持審慎的質疑,而那些拿猶太人身份與災難歷史做文章的政治主張或民族主張更讓他完全不能認同,儘管他是一個猶太人,也自認是猶太人,卻不認為那些被認為是猶太人該有的共同記憶與主張必需在他的身上表現出來,因為他認為是一個不同於他們的猶太人.而在巴黎高等師範求學也讓他觀察到了法國知識分子特有的精神風貌.是一種過度的激情,狹隘,自負與天真,對概念的嫻熟與對現實的無能是那些法國知識分子的通病,Jud完全看不上這些,在他眼裡這些法國的高級知識分子是口語的巨人,行動的侏儒,光說不練的傢伙,甚至是表演更勝於內容的演員,以至於Judu一直都不喜歡知識分子這個稱呼.在他看來能擔當起知識分子稱呼的法國人,只有卡繆與阿宏那一代人,他們之後的知識分子只部過是代表一些學術權貴與脫離現實的精英主義而已.至於他的後來移居的美國,它的觀察也毫不留情,Judt以情人來形容美國.美國若即若離,即便到了中年,體重超標且妄自尊大,它仍余有一絲風韻,對審美疲勞的歐洲人來說,它的矛盾和新奇正是殘存風韻的一部分.這塊老牌新大陸,一年又一年地發掘自己,它是躲在前工業時代神話中的帝國,即危險又單純.從以上種種的批判中,讀者將會發現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在他身上已經完全沒了痕跡.
Judt自認只是一個歷史學家,而歷史學家是靠列舉事實傳道的哲學家而已,或許是這種自省,年輕時代的馬克斯主義的信仰者不但蛻變成僅信仰左派唯一還能信仰的部分,也有了一些與他年輕時完全不同的觀察.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以菁英者的角度重新審視英國均等教育的矛盾性,把機會的均等提到更高的層次,而放棄了結果的均等,起碼他認為結果均等的教育是英國高等教育完全衰敗的最重要因素.從此觀之,雖然他也不認同市場主義的狂熱影響,但是對一個曾經極端的左派而言,這已經是非常不容易的,特別對一個菁英知識份子而言,這絕對是鳳毛麟角個案,這種從現實觀察得來的轉變絕對不是單純的對現實投降,而是有它深遠意義.
雖然這只是本小書,只是一些生活過往的回憶,但單純以回憶錄而論未免太小,文本內容所顯出的思想變革與精神絕對超越許多所謂的鉅著,更與那些思想巨人與主義之父所言有別,因為作者就是要推翻這種純種的,集體的,烏托邦的,轉為混合的,邊緣的,且雜亂的個體自我.看完這本書,再對比於當前現實社會中的知識分子,文人,還是那些所謂的菁英份子所表達的各色主張,將會發現Judt唾棄的空間正充滿在我們周圍,不論是媒體,還是書籍中,已至於我以為這本書繁體版的出現本身就是不可思議的.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