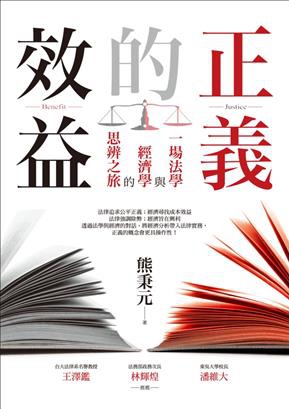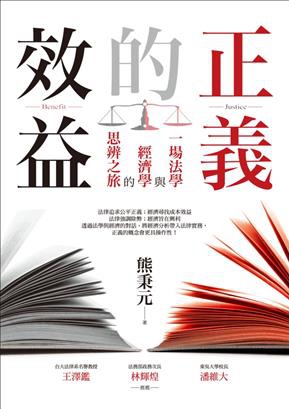
正義的效益:一場法學與經濟學的思辨之旅(熊秉元)
The Demand for Justice is not independent of its price.
黑貓白貓,只要是波斯貓就是好貓.當然,這說法可能跟大多數人聽過的,只要能捉老鼠就是好貓大不相同,不過這根本沒有影響,好貓如何認定本就因人而異,沒有人一定不變的道理,進一步說,對一群人來說,好貓如何認定,因人,因時,因地,也會有不同的答案,比如鼠患嚴重,捕鼠方式選擇不多,滅鼠效率不佳的古代,或未能機械化的農村,會捉老鼠可能更被視為是好貓的條件,相對的,對於古代宮廷貴族或是現代的城市小資階級,波斯貓可就比捉老鼠受到矚目.需求人人不同,也會隨地點,時代的不同而有所改變,甚麼是好貓,自然沒有一定的答案,即使有,那也是那個時代的,不是永遠一貫不變的
開頭的那句英文大約就是本書的主旨,這裡的困難不在Justice,而是在看到Justice竟然也要考慮its Price,應該絕大多數人會把這本書跳過,正義還要考慮它的價值,進一步說,正義還要考慮它的成本效益問題,用更流行的語彙,正義還有cp值排列的可能,當然不可能被接受,君不見近年流行的經濟書籍,從Michael Sandel,Thomas Piketty,到近日的Anthonty Atkinson這些作者,他們的作品清一色有個共同的書名,我把它叫做"經濟的正義分析",而這一本熊秉元的書籍則恰好相反,可以稱之為"正義的經濟分析".把正義套上價值,價錢,尺度,排序,在出版或社科思想主流世界來說簡直是件大逆不道,又荒唐不值一讀的.因此閱讀這本書真正的困難,不在分析,而在信仰,信仰的差異是你的神與我的神,你的教義與我的教義,都是不能共存的,但其實他們只是在同一個人身上不能共存,但離開個人卻是可以的,不同宗教的神或教義雖然彼此衝突卻能同時存在,否則這世界就不會有許多不同的宗教,且各自擁有信徒,因此,正義能不能評價並不是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你認為不行,卻有人認為可以,即你的波斯貓與他捉老鼠的貓並沒有誰是好貓的問題,單看主張者自己的價值,與喜好而定.而既然正義人言人殊,如果不能確實定義一個正義的標準範疇,討論分析及無標準沒有意義,所以,這本書是試圖將經濟分析的方式引入法律中,更進一步說,是希望能透過經濟學的分析方式來對法律的實務與程序產生更進一步的影響.
正義如何定義?公平如何裁判?作者首先試圖釐清一個問題,人們之間不言自明的規則或法律是如何來的?是某個偉大政治人物所設立的?抑或是某所謂的先王聖賢所創立的?事實上都不是,它的產生是人類生活從個人到部落到國家出現的過程中,從實際的生活中逐步建立起來的,並沒有任何個人聖人能在正義,公平,道德,法律的定義上存有絕對的權威,或唯一的定義權,柏拉圖沒有,孔夫子也沒有,那就更別說是Sandel了,而任何一種以上的價值也沒有歷來不變而不與時俱進的,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東亞社會的孝道,如果不曾與時改變其內涵,我們將很難脫離原始封建,或是各種阻礙現代化的思想與條綱,社會的僵固性將比當前看到的更大,東北亞社會的進步除了經濟發展外,正是擁有這種逐步將傳統道德內化成更符合當代的限制的真實轉變,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教條價值,孝的目標與方式皆與過往不同,但孝的概念仍舊被保留下來,正是明證,道德不是聖王所說或是一個被規範不變的條綱,而這本書中熊秉元試圖先從聖王論vs生活論,從規範論vs實證論來說明這種從實際生活裡所體悟產生的道德哲學,乃至規則,與法律,不是聖王,規範產生,而是從生活裡來的,既然如此,我們是否有理由必然絕對奉行羅爾斯或是桑戴爾的正義論貴絕對圭臬?或以此處理正義或法律的分析?答案當然是否定.至於法律的經濟分析,它的目的則更非去裁判道德原則間,或公平正義定義的差異,作者在此引出指出法律的目的不在裁決處理公平正義,而在處理不同價值的衝突,這裡所謂的價值並不是指經濟價值,而是法律判決對於社會的影響等層面,即法律的經濟分析就是基於更好更便利的生活規範而來,也是從實際生活而來.
作者直言法律功能未必在於處理公平正義,而是在處理價值間的衝突,且其根本應該從社會實況中求,比如人們可言世上沒有比生命更高的價值,因此沒有人可以立法以法律令他人死亡,也可以說因為怕誤判會害死無辜之人,或基於其它等等理由而主張廢死,但深究其意,我們也可以這樣問,無辜被害者算不算人命?有沒有人因為出獄的殺人犯而被殺死?顯然,這個社會確實有人因為誤判致死,比如士兵姦殺女童案,但同時,確實也有殺人犯出獄後再殺死兩人,比如彰化女童姦殺案,無辜被害者的命若等同於加害者的命都是生命最高的價值,那麼我們怎麼能夠從這兩者當中評斷出誰的道德哲學就是必然正確,或高出?你可以說誤判的可能,我也可以說這可以藉由審判程序,比如輔以陪審團制而改善,你可以說生命最大,無法律能判死,我也可以說,死者最大,無人能令社會其他生存者時時懷滿恐懼.這兩種價值明顯就是衝突的.甚麼是公平,如何稱正義,根本是各說各話,作者於這裡引入了經濟,引入了效益,它的目的,不在處理道德高下,而在處理價值衝突?這裡一看到效益,或是經濟,很多人直覺皺眉,以為是那種算計錢財多寡的反映,殊不知它處理的價值衝突,正是前面所說的那種,誰的生命該被保護?該怎麼保護?有沒有他必然的取捨?那些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所提的善德是沒有特別該被尊崇為先的道理,作者強調先了解社會,再了解法律,讓證據說話,不是讓先王聖賢說話,道理淺中求,真正道理在家常中,而我要說一句,即使那先聖王先賢的價值也是桑戴爾,羅爾斯比較論述而來,只不過以文字處理,它的背景依然是比較,排序,論其內涵的效益與範圍,本身就是經濟方法,只不過那些價值排序靠的一半是習俗傳統,一半是桑戴爾等人的自由心證,而人們卻誤以為那是知識份子的絕世武功,其實其中仍不脫如何定義好貓的基準.,.
透過法律的經濟分析,在處理法律爭議時,有一個成本效益的根本,這裡的成本效益與金錢無關,它就是價值排序的比較,而價值會因為時間,時代的演進而有不同的改變,而從實務面來說,它可以進入實際斷案的應用,如涉及物權債權的民法,原就是涉及處理"權利"的問題,透過法經學能產生邏輯條理更符合現代社會價值的,作者希望立法或審判能在教義法學外,另佐以社科法學為基礎.從此處,他將經濟分析引入了對罪刑法定主義與無罪推定論的探索,解破了這兩個名詞本質上的無意義,但實質上卻推論出該如何處理他們在實務上該有的角色,純粹的文字思辨實在無意義,法律靠的並非信念與規範,而是事實與實證,正因為拘泥文字,才會有涉貪一審被判重刑的檢察官能提前逃亡海外,才會有做偽油還能無罪的可笑結果,實質正義程序正義都不該只是文字,紙上談兵,法律即規則,規則即是工具,概念也是工具,工具要選好的用,概念亦然,信念最好基於事實,而非想像,公共政策與法律判決最好基於事實,而非想像,而法經學或是探究法律的效益就是一種將概念工具化,將想像事實化的一種做法,它非唯一,也不是絕對正確,但終究是化概念為實務的一條路.
作者說知識是一種力量,無知也是;我們處理過去,是為了未來;選擇性記憶是處理過去,選擇記憶是處理未來.這幾句話頗有深意,雖然它沒有直指經濟的正義分析是選擇性記憶,卻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改變思維意是如此,先了解社會,再了解法律,讓證據說話,因為多言無益.社會科學亦當如此,不了解社會,只遵從聖賢條綱,如果只是在學院裡研究發揮那也罷了,它為害的範圍不過限在學術期刊或學院權位的爭奪上,但若貿然以全社會為實驗對象,它為害的範圍恐怕就難易估計,作者結論"為了正義,可以天崩地裂"是信念非事實,是文學世界裡的法律,而本書所述的正是開頭的第一句英文.以上